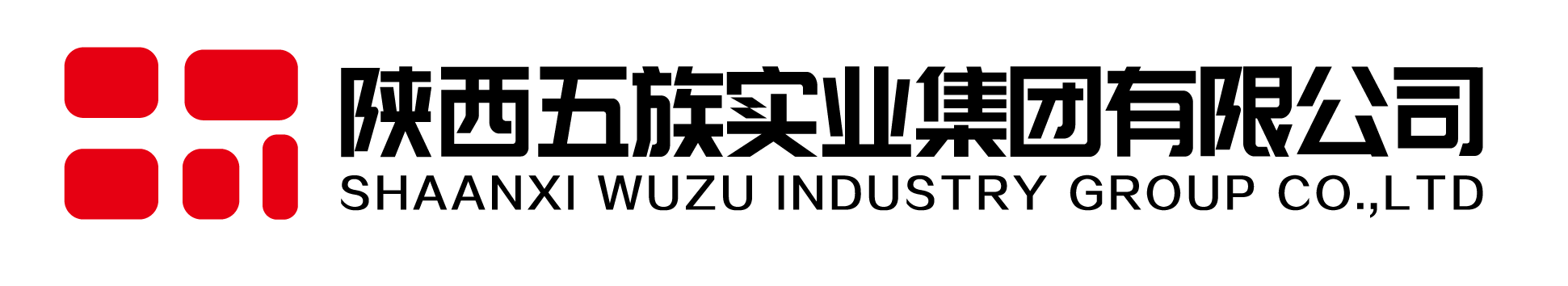若有媒介可做引线
能将华夏千年文化牵引成珠串
那这媒介的名字
或许可叫做“酒”


华夏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中,总不乏酒的身影。
纵看文体,不限于诗,词,歌,赋,曲,铭,骈文,散文;
横望感怀,人生之失意,得意,感物,怀人,送别,婚嫁,祭祖,奉天。
这些作品中,
或以酒会友,佐以知己,辅以笙歌,彻夜歌台暖响;
或折柳为信,劝酒一杯,西望阳关,从此故人难见;
或采瓠一枚,交颈合卺,宜言饮酒,守望琴瑟之好;
或宦海沉浮,终年劳牍,放甲归田,念花间酒一壶;
或春夏祈谷,秋收百子,其实酿酒,礼奉天神地祇。

远溯西周就能发现,酒早已在周人的生活中占领了重要的位置。

《周礼·天官·酒人》中便写到祭祀之酒:“酒人掌为五齐三酒,祭祀则共奉之。”
而后随着社会的演变与进步,先前用于祭祀的酒,慢慢受到各阶层人的喜爱,进入了生活中的各个领域。

如《诗经·郑风·女曰鸡鸣》写到的婚爱之酒:“宜言饮酒,与子偕老。琴瑟在御,莫不静好。”

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中的祝寿之酒:“为此春酒,以介眉寿。称彼兕觥,万寿无疆!”

再如《诗经·小雅·常棣》中兄友弟恭亲友和顺的家宴之酒:“傧尔笾豆,饮酒之饫。兄弟既具,和乐且孺。”

酒之于寻常百姓家尚且如此,之于向来偏好用嘉礼接待外族使者的周王朝统治阶层来说,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以一场飨宴之礼,请四方之宾客,不仅可以化解与外族的矛盾与隔阂,更加彰显了周朝作为礼仪之邦的仁明与宽宥。
然则物极必反,盛极而衰。当人的情绪不加克制,放任酒与意气丝丝入扣,社会与生活同样也会遭受反噬。

西周末年,王室式微,社会动荡不安,统治阶层内部荒废国政。君臣皆沉湎于酒,用以麻痹自己的神经。消极而奢华的酒宴被大规模举办,号称礼仪之邦的周朝在这个颓废的时期,丑态层出不穷。
《诗经·小雅·宾之初筵》中就便有三章记载了西周末年周人在宴会上饮酒无度的失德行为。

意为:在宴席开设之初,宾客们都是一副温良恭俭,谦逊低调的样子,因为众人尚未醉酒,便会顾及礼仪与尊严。然而醉酒之后,可谓群魔乱舞,有人酩酊大醉,举止轻佻,丝毫不顾及自己的尊严,或流连于宴席中手舞足蹈,不用礼仪威严抑制自己,举止轻浮,放浪形骸。这就是饮酒无度,枉顾礼仪秩序之祸。

意为:众宾客醉酒之后,吵闹不迭又喧闹不止。因醉酒而歪斜倾倒的身体乱挥乱抓,打翻了宴会上的笾豆。喝醉之后,乱了神志,根本不知道自己做出来了哪些失德的行为。头上的帽子歪斜脱落,还手舞足蹈,不断歇斯底里地狂呼。如果喝醉了酒就及时止损,告别主人,这对于双方来说都是福分,如果喝醉了酒,还张牙舞爪不肯离去,则是道德败坏之举。饮酒是一件雅事,要维持好自己的仪表礼节。

意为:宴会上的饮酒之事,有宾客醉酒,也有宾客不醉酒。酒宴之上会有监酒官和史官,用以端正无度饮酒与劝酒的行为。喝得酩酊大醉自然不是好事,也有人不醉酒不满意。好事之人不可以殷勤劝酒,让人酒后失态。不合乎时宜的话不能随口说,空穴来风的话也不能传诵。酒后失德之言,要他去拿没角的小公羊以示惩罚。三杯醉倒,再好事劝酒就不合适了。

西周末年,宴饮活动所肩负的积极意义已然阑珊。素以礼仪之邦著称的周王朝,在靡糜颓废的风气之下举办的宴会只有纵情声色,连监酒官的存在都无法规正和监督宴客的酒后德行。
对镜自鉴,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与周王朝的消极倦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,可也是周人的消沉与放任才造成了那些层出不穷的丑态。

华夏隽永的文明
对君子修德一则向来有自己的准则
修身养性,见贤思齐
忌骄佚奢淫,贪纵成痴
若放肆贪纵,酒便是穿肠毒药
若克制自省,酒便是无言良友
人生路远,勤记
克己复礼,宽宥及人
为人生上计

扫二维码用手机看
联系地址:陕西省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七路西北国金中心A座13层
©陕西五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陕ICP备2021012623号-1
网站建设:中企动力 西安

 029-89298003
029-89298003

 在线留言
在线留言